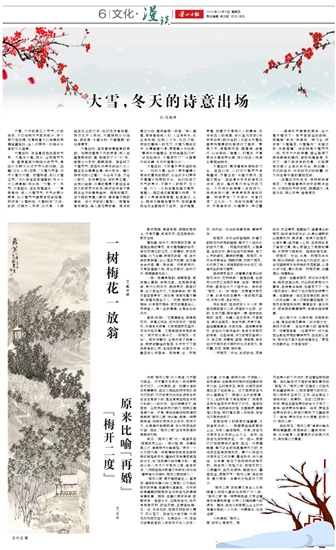文/马晓炜
大雪,冬天的第三个节气,它的到来,不仅说明天气越来越冷,仲冬摁下启动键,还意味着冬以诗意的表情隆重登场,给人们带来一场异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大雪出场,洋溢着古色古香的气息。大雪与小雪、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映。古籍《三礼义宗》记载:“大雪为节者,行于小雪为大雪。时雪转甚,故以大雪名节。”元代吴澄在其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说:“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意思是说,进入大雪节气,天气会更冷更寒,比小雪节气里更有可能降雪。民谚有“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之说。此时,对南方人来讲,这只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文字,他们无缘看到雪;而对北方人来说,大雪早就纷纷降临,满目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景象。
大雪出场,呈现着诗情画意的美韵。如果说雪是冬天的使者,那么在晶莹剔透的“雪”前面添了个“大”字,愈显纷纷扬扬、飘飘洒洒。难怪到了大雪节气,那些吟风弄月的古代文人墨客总会触景生情,诗兴勃发。唐代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全诗以幽僻、冷清的雪景勾勒出生命巨大的寂寥与孤独,映衬出作者不肯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同样的雪花,在不同的赏雪人眼中,竟有着不同的意味。宋代卢钺的《雪梅》:“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诗人借雪、梅争春告诫人们: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在边塞诗人的笔下,大雪飞舞在边关,也覆盖着大漠,更显高冷与壮美,“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大雪出场,飞扬着欢声笑语的快乐。一场场大雪,给农人带来憧憬小麦丰收喜悦的同时,也给孩子们带来尽情嬉戏玩耍的欢乐。他们忘却了天气的寒冷,不顾大人的规劝,五个一堆、六个一伙地在雪地里滚雪球,堆雪人,相互追逐撒雪嬉戏玩耍。尽管个个弄得浑身是雪,脸蛋通红,头上、脖领处腾腾地冒热气,却把童真和灿烂全都释放了出来。当然踏雪、赏雪、玩雪不仅是现代人的最爱,还深受古人的追捧,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对当时人们在冰天雪地里赏玩雪景的场面进行了描写:“豪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装雪灯,以会亲旧。”堆雪人、打雪仗,尽情享受冰雪世界乐趣,可以说古人玩得也是相当嗨皮。
大雪出场,赓续着美食美味的习俗。自古以来,人们对大雪节气很是重视,尽管各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在漫长岁月的演变沉淀中,进补、腌肉是约定俗成的习俗。冬天进补能提高人体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使畏寒现象得到改善。民间素有“冬天进补,开春打虎”“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的说法,于是涮羊肉、炒糖栗子、烤红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美食,给大雪天增添了一抹芳香四溢的韵味。而腌制“咸货”则是另一种习俗,民谚有“小雪腌菜,大雪腌肉”“未曾过年,先肥屋檐”,说的就是大雪节气一到,家家户户的房檐、窗台挂满了颜色鲜艳的腊肉、香肠和腌鱼等,形成了一道冬季独有的风景。这些带有浓郁乡土色彩的风俗,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渗透到我们的味蕾,成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密码。
“白雪欲求吟咏句,穿枝掠院演梅花。”大雪踏着朔风劲吹的鼓点出场,这种出场气势如虹,磅礴盛大,绮丽多姿,用心欣赏,皆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