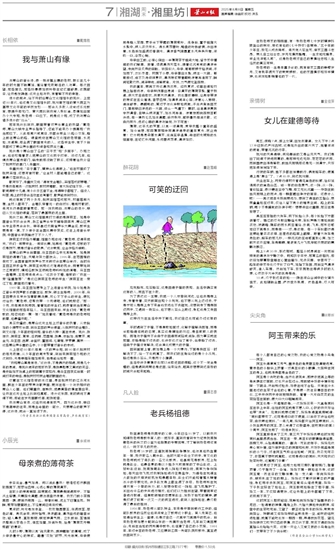■戴增胜
与萧山的音乐缘,像一株深植土壤的老树,根系在几十年的时光里不断蔓延,缠绕着无数鲜活的人与事。每次回望,那些面孔、那些场景便如枝叶般在记忆里舒展,浓荫蔽日,让我愈发确信:这片土地与我,有着解不开的牵挂。
缘分的起点,绕不开时任萧山文化馆馆长的姚俊。上世纪80年代,他还是文化馆馆长时,杭州群艺馆的黄大同正为基层文化干部的学历发愁——那会儿多数人没受过系统教育,想提升却无门。黄大同找到我爱人张松渝,恳请她出面办个大专班,张老师一口应下。就是这个班,成了我与萧山诸多缘分的“线头”。
那年姚俊找到我,眼里带着对声乐事业的热望:“戴老师,萧山太缺专业声乐指导了,您能不能来办个提高班?”我当即应下。从此每周六或周日,我都会乘坐15路公交车,踏上前往萧山的路。课堂就设在萧山文化馆的老楼里,水泥地、木桌椅,却坐满了眼里有光的人。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了萧山声乐圈的引领者和顶流力量。
姚俊是个萧山出了名的“实干家”和“多面手”。办班之余,他总琢磨着怎么把萧山的文化底子打牢。没过几年,他调去萧山宣传部门,临走前却没断了联系,还特意给我介绍了航民村的掌门人朱重庆。
朱重庆说:“日子富了,精神头也得跟上。”他在村里修了航民宾馆,还想写首村歌,“让全村人都能唱自己的歌”。这事最终落到我头上。
歌写好了,朱重庆又说:“得有支合唱队,宾馆落成时要唱。”于是我每周去一次航民村,教村民唱歌。有大妈记性不好,一句歌词得教十几遍;有小伙子五音不全,练得嗓子都哑了。但没人叫苦,晚上的村委会活动室总亮着灯,歌声能传到村口。
就这样跑了两个多月,航民宾馆落成那天,村里搭起大棚,全村人都来了。合唱队穿着统一的白衬衫,唱起村歌时,连河水仿佛都跟着晃悠。那一刻我明白,与萧山的缘分,早已从文化馆的课堂,落到了最基层的泥土里。
姚俊之后,萧山文化馆里常打交道的是颜莉亚。她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声乐专家辅导团团员、萧山区声乐专业委员会会长。早年拿过云南省声乐大赛金奖,教学生更是有一套,不少弟子在全国比赛中获奖,还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输送了不少人才。
颜莉亚对我格外尊重,馆里办班总说:“戴老师,您得来把关。”我们一起带学生,一起评比赛,她常说:“戴老师,您教的不仅是技巧,更是对音乐的敬畏。”这份默契,让合作格外顺畅。
在萧山的声乐后辈里,马亚囡的名字尤其响亮。她是颜莉娅的得意门生,天赋与努力都拔尖。1995年,在范国强的促成下,全国首届民族声乐艺术研讨会在萧山举行。当时马亚囡正积极备考,颜莉亚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特意带她到之江度假村,请知名教授王炳锐老师听听她的演唱。马亚囡一曲唱罢,王老师连连点头:“这孩子不错,谁教的?”我在一旁“隆重推荐”:“是这位颜莉亚老师的学生!”颜莉亚在一旁红了脸,眼里却闪着光。
1997年,马亚囡如愿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如今她是浙江音乐学院声歌系的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年,马亚囡要去北京参加青歌赛决赛,放心不下手头的学生,便托付给我:“戴老师,您帮我带一个月课吧,他们就服您。”那一个月,我每周去杭师院,看着她的学生们,就像看到当年萧山文化馆里的那些年轻人。马亚囡回来后,学生们说:“戴老师教的,和您说的一模一样!”她笑着说:“戴老师是我的老师和前辈,他最懂我啦。”
其实我懂的,是萧山这片土地上对音乐的执着。从史晓如的小提琴弦乐团,到马亚囡的声乐课堂;从航民村的合唱队,到文化馆、少年宫的培训班,音乐的火种一直在传递。姚俊、陈祥云、颜莉亚、莫军、汪炳辉、范国强、陈晨、史晓如、吴慧芬、周金元、马亚囡、吕薇、徐益欣、董丽鸿、毛建强、罗素霞、高辰……这些萧山声乐圈的名字,个个都带着对音乐的赤诚。
从上世纪80年代每周一次的声乐班,到90年代航民村的每月数趟;从少年宫的周末聚餐,到后来颜莉娅办班的次次到场,光是单程车程加起来,怕是能绕地球一圈。
“我和萧山真是有缘。”这份缘,不是偶然的相遇,而是几十年的浸润。是姚俊递来的那杯热茶,是陈晨憨厚又真诚的笑容,是史晓如家饭桌上的那碗霉干菜扣肉,是马亚囡获奖后第一时间打来的电话,是航民村村民合唱时眼里的光。
它藏在文化馆老楼的木纹里,浸在航民村的红汤河水里,飘在少年宫的琴声与歌声里,更刻在每一个与我相识的萧山人心里。他们尊重我,信赖我,把最真挚的情谊捧出来,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归属感。缘分这东西,有时候说不清道不明,却能在岁月里酿成酒,越陈越香。
我与萧山有缘,这话我说得有底气。因为这份缘,早已不是简单的往来,而是生命里的一部分。只要萧山的歌声不停,这份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系原浙江歌舞团著名男高音、声乐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