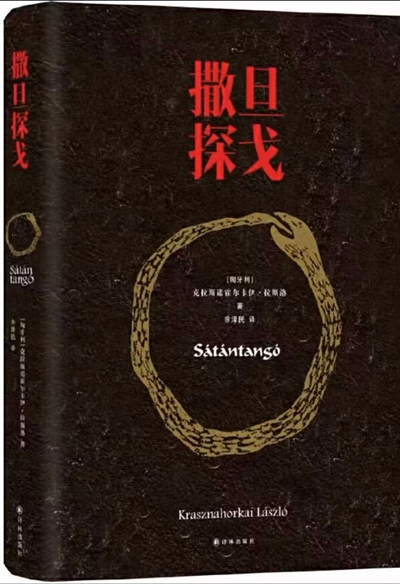文/龙烟
20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没错,这个名字极其拗口,但跟他的作品比起来,已经算明白如话了。
文学自20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尤其是西方文学,已经在抛弃读者、自说自话、玄虚晦涩的路上一路狂奔、越走越远。
按他们的说法,传统的写作,到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手里,已经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把所有能写的都已经写到了尽头。
现代作家只有另辟蹊径,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巨大的革新。于是,现代小说的故事情节、可读性越来越淡化,对哲理、生命、心理的挖掘和对前沿写作技巧的探索,则越来越深入,不可避免地与普通大众拉开了距离。所以,读现代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相比去年,今年的拉斯洛,远在东欧,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迥异,写作风格深受西方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影响,阅读门槛变得更高,连向普通读者介绍他的作品,都成了一桩颇费踌躇的难事。
甚至连他作品的中译者都说:“读这本几乎不分段落的小说,就像读没有标点的古文,每读一行都感觉艰难……这本书于我,是一种虐读。”(译林出版社《撒旦探戈》译者序)
虽然想要深入浅出地介绍他的作品,是一桩难事,但总要试试。今天先从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入手。
《撒旦探戈》的故事情节,捋清以后其实很简单,甚至有点“无厘头”:
它就讲了一个没落村庄里的村民被骗的过程。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村庄中,这里与世隔绝破败不堪,充满着无尽的死寂与绝望。集体农庄已经耗尽了村民的生活热情,让他们只有通过偷情和相互算计来获取残存的快慰。在集体农庄即将解体之时,村民们密谋贩卖了集体的牛并试图携款潜逃,去追求所谓的黄金世界。一个哥哥甚至骗取了七岁妹妹的所有钱款,导致妹妹绝望自杀。这时候,从城里来的两位“救世主”伊利米阿什和裴特利纳蛊惑了他们。这两位与政府合作的骗子,宣称可以带着村民走出生活困境。他们以调查小女孩的死为由,展开了一场先知般的演说,并顺势榨取了他们的钱财,把村民带到城里各个地方,从事所谓“神圣的工作”。当村民们背井离乡、断绝一切后路,流落到城市,才发现从事的居然是“持续而警觉地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严密记录下所有人的看法、传言和所发生的事件”,完全看不到希望。在一段无望的抗争之后,村民们梦想破灭,不得不重新回到更加破败的乡村,陷入更加绝望的状态之中。
小说将骗子视为“撒旦”,书中有村民被洗脑后跟随骗子跳“探戈舞”的一段情节,就是书名的来源。
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说它读起来很难?主要是它特殊的写作手法和丰富的政治隐喻。
关于写作手法,一方面,作者以碎片化的形式将故事做了空间和时间上的切割,从不同侧面以空间为中心建构事件。而且,在碎片化叙事中又不乏散点叙事,比如医生所见和施密特家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事件,这样就形成了空间叙事、碎片化叙事和散点叙事的复杂交互逻辑。
另一方面,“医生”的设置丰富了小说的叙事人称,整部小说是第三人称叙事,但“医生”出现时,作者会有意识地引导读者跟上“医生”的“主观镜头”,转换成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的视点在“自我”和“医生”中游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小说的“环形结构”。小说采用“探戈舞步”的叙事结构,即“六步前进,六步后退”,形成循环往复的节奏,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小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另一点,是它的超级长句。
“秋日的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在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搪瓷面上,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继续沿着那个无休止的、封闭的飞行路径不停地盘飞,直到电灯熄灭;一张富于怜悯的手托着那张胡子拉碴的脸,这是酒馆老板的脸;此刻,酒馆老板正听着哗哗不停的雨声,眨着昏昏欲睡的眼睛盯着飞虻愣神,嘴里小声地嘟囔说:你们全都见鬼去吧!”连译者都说:“读这样的长句,与其说是中文,不如说像太极拳,缜密沉着,缠绵不断,节节贯串,是中文写作者凭中文思维不大可能写出来的中文。”但这样黏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的句子,却无比贴合小说中的氛围,把那种绝望、压抑的感觉描绘得丝丝入扣。
关于小说的“政治隐喻”,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外来人”欺骗的“本地人”故事,联想到匈牙利的历史大部分都处在“外族”的控制之下,是否就是匈牙利历史的象征?其中的“农业合作社”等背景以及对村民一切行动的监视,难免让人联想到二战以后该国的极权高压时代;而骗子提出的“投资资本”及至最后的破产,是否也在暗示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一个被骗的过程……可以引发无数联想。
当然,有一定阅读储备的读者,更能从中读出纯文学的快乐。书中大量的隐喻、象征以及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手法,可以从中看到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子。
小说绵密深邃的细节与心理描写,则又继承了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经典作家的传统,让作品增加了一层可喜的厚度。
总之,这是一部需要极大耐心来细品的小说。听说还据此拍摄了一部长达七个小时的同名电影,尚未领教,或可同作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