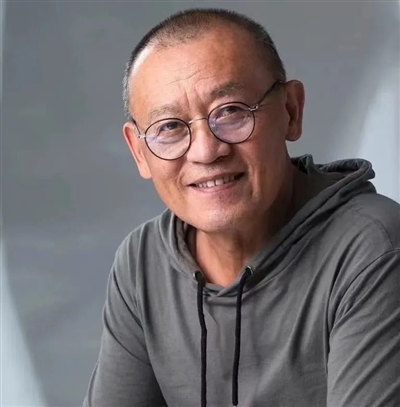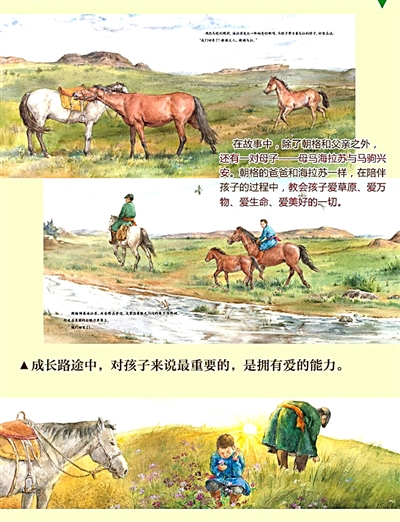编者按:
最近,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唤起了人们对草原的无尽向往。草原的风、马、羊群、牧民,就像是一首永远都唱不完的歌。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也是一位把对草原的热爱融入文学创作的作家。
席慕蓉说,他的文字里藏着一种文化上源远流长的观看的角度与生长的态度;张晓风说,他的“咏物散文”,就算放在康熙王朝所编的历代咏物诗选里也是毫无愧色;腾格尔说,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好像草原就在眼前。
文/ 周秀国
1
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我陷在柔软的沙发里滑动手机,无人打扰。就这样,我翻到了《万物凝视》。看到开篇《蝴蝶给波斯菊写信》第二句话:“主人阿拉木斯的两只小山羊恋爱了”,就把我给看乐了,心想这小山羊也太调皮,主人养羊目的是出售赚钱的,你们怎么还恋爱上了。当然这是人的杂念,作为蝴蝶,它没有这个想法,它纯出于好奇、羡慕,当然还有点八卦。整封信,蝴蝶都在向波斯菊絮絮叨叨自己偷窥两只山羊恋爱的事,同时又吐槽了自己的一些事:说自己最懂恋爱,又说没有哪只蝴蝶爱上它;说胡蜂在追求它,又说胡蜂嗡嗡的只配和苍蝇恋爱去;把山羊恋爱的事告诉了啄木鸟,又说啄木鸟不解风情,诅咒啄木鸟没有爱情。最后蝴蝶奉承波斯菊是最懂浪漫的花,目的就是想让波斯菊告诉它两只山羊是不是在真正恋爱,为此还表露心迹:如果这里(万度苏草原)没有恋爱者,我选择离开,去有爱情的地方。至此,一只骄傲自负对爱情充满幻想又爱而不得只好偷看山羊恋爱的恋爱脑蝴蝶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又心生怜爱。
读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乐不可支的,愉悦极了,状态是激动兴奋的,很想到街上拉个人过来一起分享这份可爱和美好。确实,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还从来没看到过蝴蝶写的信,没想到过蝴蝶能用如此轻灵稚趣的文字袒露心声。这些文字源源不断地给予了我美妙享受,让我迫不及待想往下看《波斯菊的复信》,看《野蜜蜂给月牙的信》《月牙给野蜜蜂的回信》《土拨鼠给闪电写信》《闪电给土拨鼠的复信》……从那个冬日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已经从《十月》《当代》《天涯》《人民文学》《文艺报》《芙蓉》《广州文艺》收集了近40封这样以“万物”为开头标识的信,来来回回细读了好几遍。
对于我这样的业余读者来说,这些信是非常容易进入阅读状态的。它们不是靠离奇的故事、重重的悬念、惊险的情节、激烈的冲突来引诱读者欲罢不能的,也不靠晦涩高级的文字、朦胧深奥的暗喻、前卫潮流的“主义”来教导读者顶礼膜拜的,在我看来,除了那天有适合阅读的天时、地利、人和外,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幕后作者——鲍尔吉·原野先生——有颗宝贵的充满博爱、童真、赤诚的心。这颗心,能让你在阅读草原上那些鲜活生命柔情似水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命运时,不断遇到惊奇和美好。因为博爱,所以草原之上的万物,无论是花栗鼠、灰兔、太平鸟、麦穗鱼等动物,绣线菊、白桦树、落叶松、朝鲜白头翁等植物,还是四胡、马头琴、椴木碗、拴马桩等造物,都得到了他的关爱和垂怜,“他把心匍匐在草原上”,倾听它们的喜怒哀乐、疑难困惑,并通过“信”的形式为它们代言,告诉它们,其实也是我们(万物),要互相“凝视”“相望”“交谈”“亲近”“歌唱”“相伴”“低语”。信与回信之间,是真诚满满的问候和关切,弥漫着爱的气息。我的心就这样在字里行间被这种万物间的爱给慢慢融化了。因为童真,所以他笔下的万物,都拥有儿童才能有的无忌、天真、好问、想象力丰富等特质,这让它们的语言闪耀着童趣、无邪的光芒。蓝窗帘可以直接说金牙“并不像大公鸡说的那么值钱”,门竟然问风“你会闭上眼睛,把头放在一块石头上入睡吗”,太平鸟告诉落叶松“我只吃过一个花楸果,吃过再吃一个,永远是一个”。我们都喜欢和孩子交谈,孩子的语言虽然简单稚嫩,但天然去雕饰,就像他们肥嘟嘟粉嫩嫩的小手,光洁可爱,最能激起你心里原始的爱意。这样的语言更有力量,直抵人心,让你爱心、柔情泛滥。也因为赤诚,所以他笔下万物之间所有的信都是直抒胸臆的,没有掩藏,没有矫揉造作。这需要一颗对草原爱得多么深沉的赤子之心才能做到啊,他熟知这里的一切,对它们饱含深情,却抑制自己甘愿躲在幕后,让万物走到前台发声。赤诚让一切变得真实、自然、可信,就像是你自己趴在草丛中、站在溪石上,聆听万物没有经过人类加工过的交谈和歌唱。如此,我们的心直接地就随着拴马桩因为拆迁可能被劈了烧火的命运而悲叹,为土拨鼠不被外地人屠杀而祈祷,同时也为麦穗鱼能自由感受水的温柔与爱意而舒心,为马头琴奏出的优美长调而激动。但是悲叹祈祷也好,舒心激动也好,最终在我们心里不断激起的是对草原万物咆哮般的爱,恨不得拥之入怀细细抚摸的爱。这种情感真挚而真实,产生的震撼直击灵魂,让你觉得,这就是草原万物发自内心的呐喊和欢呼。
2
这是我读完这些信时的初体验,奇幻而迷人。那种浓烈的草原气息深深吸引着我,那种万物相互问候的美好深深感染了我。我想鲍尔吉·原野先生肯定是位软装高手和优秀的作曲家,能把看似杂乱的万物串联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能听懂万物的语言并把它们谱写成如此美妙的乐章。而这样的串联、谱写,看似漫不经心、波澜不惊,却能持续带给你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对美的赞叹,最后在你脑中逐渐汇聚成一幅爱的巨像和一声爱的巨响。
除此之外,这些信中的比喻、想象,包括如前已述的语言,同样令人着迷。
信中的比喻,新奇、精妙、传神。这是伟大的作家才具备的才华,他们不允许“岁月如梭”这样泛着古董气息的比喻出现。在这里,马尾鬃像一只翅膀蓬松的雄鹰,太平鸟的羽冠看上去像一个西藏喇嘛,河水的波纹像漂过来许多弯曲的金线,羊群像一片翻滚的白石头,阳光的暖意晒在后背好像小蚂蚁在爬,牵牛花像一条被风吹开的裙子。这样的比喻在信中随处可见,宛如一颗颗亮丽的宝石。
令人佩服的是想象。这些信,其实通篇都是想象的产物,但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想象都是那么真实可见,好像事实就是如此,这是万物真实的情感和性格。要说一封信能做到如此并不神奇,可这是几十封信啊,得需要什么样的脑洞才能做到。每封信,从第一句问候语开始,想象就开始像脱缰的野马,汪洋恣肆,喷薄而出。这里我想暂且借用写作手法中的意识流这一概念,把这样的想象称为想象流,像奔腾的流水一样酣畅有力。但这种“流”,并不杂乱,而是紧紧围绕情感的表达展开,让想象具有飘逸灵动同时又情真意切的鲜明特征。
最喜欢的还是语言。尽管前面已有所论及,但我忍不住还想再着重论述一下。阅读信中文字的时候,我脑海中常常浮现出杨万里的诗。在我看来,他的诗,鲍尔吉·原野先生的信,虽然文体不一,在语言上却有高度相似的特点:奇趣,新奇有雅趣。试看《午热登多稼亭(五首其二)》:
矮屋炎天不可居,高亭爽气亦元无。
小风不被蝉餐却,合有些凉到老夫。
炎热的天气里,一个老头正与蝉争风。寥寥几字,神态、意境已跃然纸上。更绝的是,里面有种“趣”在,是生活的情趣、士人的雅趣。评论家把诚斋先生诗的这种风格称为“诚斋体”,“诚斋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奇趣”。奇是平中见奇,能在日常所见中写出新意和神奇;而趣,是言似稚子语,憨态可掬,理有大智慧,发人深省,巨大反差中令人会心一笑,叹绝。
3
鲍尔吉·原野先生在这些信中的语言,同样具有这种味道。这种味道,也可以借助《两小儿辩日》的故事来总体体会。无论是喜鹊与麦穗鱼,沙粒与云雀,烟荷包与黑缎子坎肩,银耳环与炕席……都似“两小儿”,而味道就藏在这些信的一来一回一问一答间。概括起来,其有“三奇三趣”。一奇是精准精炼,写麻雀就是麻雀的口吻,写云雀就是云雀的语气,写喜鹊就是喜鹊的口音,短短几句就能勾勒出万物鲜明特点;二奇是儿童化,好奇问句多、出其不意语句多,思维逻辑跳跃多,语言简单直接,大巧若拙;三奇是势能大,有时俏皮突兀,有时一本正经,有时自说自话,呆萌可爱,有时沉稳平静,羞涩内向。这种落差使语言充满了势能,富有节奏美感。精炼的语言,让万物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写出了一种活劲儿新鲜劲儿,此一趣;儿童化的语言,用一种近似无厘头的方式解构道貌岸然、故作高深的文风,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此二趣;语言蓄起的巨大势能,能时刻冲破你的审美藩篱,体会到那种难以言表又深受撩拨的美感和情趣,此三趣。这种阅读体验很奇妙,相距800多年的文学作品,虽遥远却相通,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这些特点,使“万物”系散文与鲍尔吉·原野先生之前的散文相比,与目前主流的散文相比,都有较明显的区别。鲍尔吉·原野先生曾经在评价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与风景对话》时说:我们领略了东山魁夷所看到、所体察、所铭记的风景,除了事物的具象之外,文中还有一股说不清的潜流,勉强可以说成是淡淡的抑郁,暗藏的感恩与压低声音的喟叹,正是这股说不出来的潜流,感染着读者。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更好领略“万物”系散文独特魅力的钥匙。他总想整点不一样的,不断突破自我,所以在新作“万物”系散文中,除了新奇的比喻、奔涌的想象流和奇趣的语言外,其实还有很多新鲜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比如结构,有的围绕着“说不出来的潜流”这根主线,流露的情绪或高或低,就像交响乐,围绕着主旋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有的像蒲公英,在大大的“说不出来的潜流”这个絮球上,分布着许许多多轻盈的种子。比如视角,作者完全消失,让万物直接和读者见面,从而减少了情感传递的环节。比如细节,很少用概述、概念等含糊的词句蒙混,写树直接到野山楂树、花楸树、接骨木树、榆树,写喜鹊的呼吸和飞翔直接到数据、到科普,让草原的气息和美、万物的习性和情感,细到末梢,“潜流”自显,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威力。这些突破说明,鲍尔吉·原野先生的“万物”系散文,已经到达了他想象中的散文高度:“他并非展示天地万物,只是坦露了自己的心”。这颗袒露的心,就是那股“说不出来的潜流”。他不仅用天才的想象构筑起了一个童话新世界,也用天赋的才华打开了一个散文新世界。
最后,我还是想用鲍尔吉·原野先生的话来表达我读“万物”系散文的总体感受:它们让我懂得审美并在美里获得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