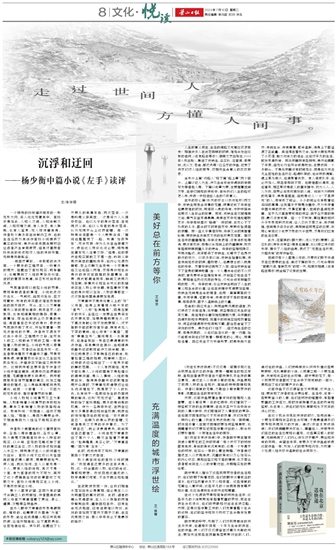文/朱华丽
一个特殊的场域编织起来的一张无形大网,将人统统笼罩其中。官场亦是如此,人和人之间,人和体制之间,人和环境之间,有人贪恋,有人挣脱,也有人窒息,无人可独善其身。作者杨少衡多年在体制内工作,他的生活经历为其创作官场小说提供了真实的场域,虽然近年来同类题材已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但其对基层官场另类的叙述和对人性的独到开掘,无疑是另辟蹊径。
一起医疗事故,一件敏感的贪污案,一个棘手的工程项目,一场意外的塌方,袒露出了官场现实、明争暗斗,也触摸到了人性的复杂与纠结,彼时的青萍与微澜,倏忽形成后来的风浪。
气氛渲染可以把控小说的节奏,更可牵制读者的情绪。小说叙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疏可行车马,密不可藏针,所有的冲突都浓缩在救援前后的四天四夜。开头,主人公万秉章痛失父亲的悲怆渲染,既来自家人的抱怨,也有知道真相的撕裂,悲情一再蔓延,可当他接到上级求情的电话,再回看自己书记的身份,悲伤的气氛陡然起了变化,开始笼罩着一层无法言说的云雾。作者并不满足于这类小冲突,工程塌方之后,生死未卜的工人和前途不明的工程一样牵扯着人物的神经,小说的气氛从悲情变得沉重。死者已矣姑且先放一边,生者等待营救才是重中之重,节奏变得急遽,顺着营救这条主线又生出无数条支线,矛盾冲突不断但又秩序井然。这种秩序感主要来自于作者对小说矛盾在铺陈、进展中内在逻辑的把握,笔酣墨饱便水到渠成。秩序感同样来自细节描摹的真实,比如工程建设的描述,让人身临其境感到危机逼近,谜团一个接着一个,一双巨大的无形的手,推动着情节的发酵。
小说人物和小说情节又互为影响,人物影响着小说情节的走势和发展,事件又影响着人物的抉择和命运。张爱玲说:“我相信人,但我不相信人性。”相信人,是因为需要合作,不相信是因为人性经不起现实的试探。
作者杨少衡营造的这个基层官场中,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各怀心事。杨少衡毫不隐晦官场中令人咋舌的现实,以冷凝、客观的笔触还原了官场的真实生态,对人物的陈述和刻画入木三分,特别是对主人公的刻画尤为出彩。官场小说不应该以光怪陆离的描述博人眼球,更需要接地气、讲人话,就比如说,主人公首先是一个人,要有人性的体现,其次才是一个官,有为官者的可为不可为,离开了这个逻辑再生动的故事都成了无根之木,官场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不是历史架空小说。
是个人都有欲望,正因为有欲望才会确立人的两面性,作者塑造的县城父母官万秉章潜藏了责任、孝心、谨慎、狡黠等各种品质。
在外人眼中万秉章的形象是硬朗的、强势的,他需要对外塑造“为官”的形象,能让他迅速融入现实并筑起防御,让组织相信他,让下属敬畏他,让百姓信任他。独处时,他露出了七尺男儿的柔情本色:两次落泪,一次是听闻父亲离世,一次是将六人从洞中救出。他以儿子的身份落泪,自觉愧对父亲;他以父母官的身份落泪,认为无愧于头上这顶官帽。每一次转身流泪都是一个人默默流泪,“据说他整整哭了一路。所谓“如丧考妣”,死爹死娘,作为儿子自当悲痛万分,像他这么哭似也没必要,特别是在基本无人注意之际。”但是,他的悲伤在现实面前又不堪一击,听到父亲骤然离世的噩耗传来,他内心充满负罪感,老上级韩文生来电一个求情电话又让他陷入两难,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冲突在回程的车里蔓延,自责、愧疚感潮涌而来,瞬间又被层级观压制,亲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抵牾冲突在人物心中发酵,有些事并不是他的身份可以左右,人物的情感在一次次抉择中塑造得更加饱满。
万秉章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父母官,他身上有着烟火味十足的“官气”,人称“脸黑嘴臭”,因是左撇子的关系,坐座位一定要坐在贵宾右边方便夹菜,如果弄错就要发火;对下属没有耐心动不动就要骂人,对于挂职干部邵乾好言好语,颇有点见人下菜的意味;他心中有“小算盘”,苦练“秉章左书”,据说等北一水库建成,他准备挑出一张自己最得意的书法作品,将其镌刻在洞口;当知道县委副书记邵乾可能涉及到受贿,第一反应就是怎么不影响自己的前途,趁着检查工程的档期,和嫌疑人密谈,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一个党员干部的廉政范围。一个人有两面性,党员干部也是人,小说的塑造不是脸谱化的简单刻画,是从人情味、人性的角度出发。推测县委副书记邵乾埋在塌方山洞时,万秉章无数遍想过让他永远深埋地下,既是报了个人的私仇,也有利于一些即将发生的负面问题的解决,这叫“死无对证”。高速旋转的除了官场策略,更多的是利弊的权衡。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在岗在位有太多情非得已和利益权衡,就像他的妹妹埋怨他的那句话:“你只顾你自己”。他顾及的是头顶的官帽,又或者是来之不易的平步青云。为了“顾自己”,就必须患得患失,到后来他自己都信了。小说结尾万秉章救出了第六个人,韩文生指着万秉章说:“脸黑嘴臭,其实心软。”万秉章自嘲:“因为是‘左手’。”
此时,远远传来了鸡叫,万秉章的第四个不眠之夜告结。
杨少衡在说他的官场小说时提到:“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注目点是人物,这一场合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思想。我试图把这里边的人物写得真切可感,不流于概念和脸谱化。”
在邵乾被救那一刻,让我们相信水落石出未必是真相,但必是主人公光明磊落的高光时刻。此时,语言的镜头变得虚缓,主人公从抉择的两难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归自我。已有生命无法挽回,已有结局难以弥补,此刻的泪如雨下显然不同于之前,在狂风骤雨之后,悲从中来未必不是最好的释怀!
本版投稿邮箱:xsbqnyy1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