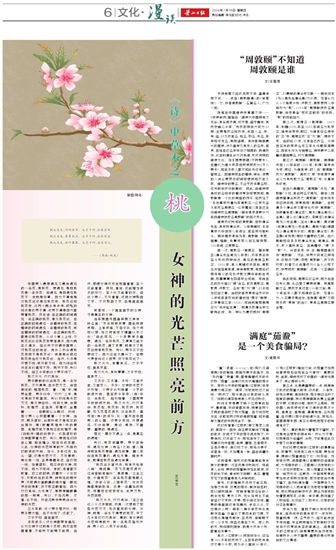文/查君书
“鲞”(读音:xiǎng),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即剖开晾干的鱼干,如“牛肉鲞”“笋鲞”等,都是腌腊成干的片状物。“茄鲞”,当是切成片状腌腊的茄子干。而我今天讲的茄鲞是《红楼梦》中写得最为翔实的一道菜,刘姥姥吃过之后说:“哄我了,茄子跑出这样的味儿来了。”说明这道菜非寻常人家见过吃过。
听说北京是最不缺少红楼宴的地方,暑假里,我到首都旅游,特意在两个不同的酒店吃了两次茄鲞。且不说好吃与否,总感觉两次吃的是假茄鲞,和书里原文描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看看《红楼梦》原文是怎么说的,第四十一回中,由王熙凤解说了茄鲞的做法: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剥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
试问诸君,谁吃过的茄鲞真能有点原文的意思?反正我是没吃到过。可能有人会说,贾府的茄鲞制作如此麻烦,你花的钱不够,肯定吃不到啊!其实,曹雪芹笔下的茄鲞是有几点疑问的。
首先,它的腌制方法并不能实现。如原文所写,初夏的茄子,制作后密封,可以随吃随拌。可稍有腌菜经验的人就会发现,夏天炎热,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它不变质,干果、茄子倒还好说,重要的是里面还有鸡脯肉,赤日炎炎,不烂等什么呢?早年八旗子弟家中也有制作豆酱、炒酱瓜丁等肉食的习惯,不过那也是腊月制作,正月吃,保鲜期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还是在冬天。那么热的天,别说随吃随拌,就是十天半个月,都算他本事大。
其次,《红楼梦》从问世到如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上百年的吃货绝对不是个小数,可为什么直到80年代,87版《红楼梦》播出之后,这茄鲞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各大餐厅?真要好吃、能做,早就变成了中国的一道传统美食了,何必等到今天。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文叙述的茄鲞太麻烦,没法做。从油炸,到鸡汤煨制,再到封存,茄子早已经成了黏腻的糨糊,而这层糨糊再包裹上坚硬的干果,这样的口感,绝称不上美味。而中国人向来讲究饮食之道中的层次分明,谁是主,谁是辅,清清楚楚,名叫茄鲞,自然要以茄子的味道为主,而鸡汤、香菌等等东西,其实也早就把茄子的味道淹没了。
那么,真的是因为曹雪芹不懂吃,不过是凭空想象的美食吗?我认为不是,反而是因为他懂吃、会吃,才故意在此处安排了这样的情境。
我们还要还原到《红楼梦》的情景当中,按情节,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贾母设宴,席间以茄鲞闹出了这一场笑话。刘姥姥示弱,进园都是以自嘲而巴结阔亲戚,大观园中的人,又都是以刘姥姥的乡下人没见识而取乐。那么茄鲞正好是这样一味药引子,王熙凤一方面用繁复的烹饪叙述来哄刘姥姥,那刘姥姥当然是不懂了,自然听得发懵,一方面贾母及大观园中的众人就爱看这刘姥姥发懵的憨样,而这荒诞的制作方法,更让刘姥姥的发懵显得可笑,这样一举多得,既刻画了人物性格,也突出了人物关系,这样的设计实在是精妙。
中华大地一直就不缺乏传说中的美食,但传说中的美食却不一定好吃,茄鲞就是一例,名气极大,但只能存在于传说里,专业厨师谁也不敢原封不动地将它恢复到食客的餐桌上。但是诸多的红楼迷们,倒是情愿去当刘姥姥,毕竟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吃背后的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