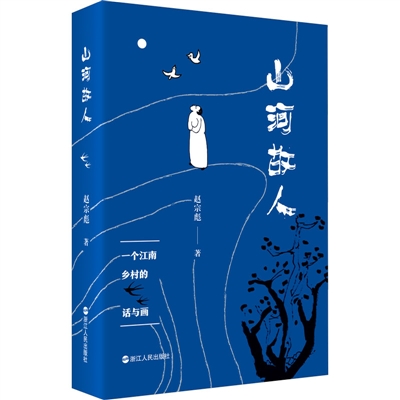文/张崇员
故乡是每个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是人的灵魂栖息地。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到赵宗彪先生的《山河故人》一书。这本被标识为“一个江南乡村的话与画”的散文集,一下子契合了浓郁的思乡情绪,我便迫不及待地网购来品读,以解乡愁之苦。
《山河故人》以浙东天台县赵宅村为原点展开、富有江南乡村特点的风俗、风物、风貌,以温和、客观的态度和小品文的格调,以114篇短小有味的千字文形式,配之以126幅黑白简笔画,推送到读者面前,文画摆布错落有致,文字风趣幽默,自然新风扑面,既为我们带来原汁原味的“乡俗民宴”,又引导我们在对江南乡村的凝视中,实现对固有乡土意象的精神回溯与对话,意味隽永,回味悠长。
作者赵宗彪有着很浓的宗族情结,对故乡饱含深情,在《山河故人》中采用回溯性视角,通过精神回溯,勾勒重现浙东山村的自然生活图卷和江南乡间的传统生活方式,如其所讲,“借着回忆,让自己来一次精神上的回乡”。
那些在故乡发生过的悠悠往事,无论是物质贫乏年代生活拮据的窘境与清苦,还是那些天真无邪、乐以忘忧的童年趣事,抑或那些受惠于长辈乡邻、影响深远的风俗礼序,经过岁月洗礼和记忆提纯,都如繁星点点,以宝藏的形式成为刻在骨血里的记忆珍藏和热辣滚烫,又如陈年老酒汩汩流出,醇香浓郁,令人心醉,沁人心脾。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天台,“多山也多水”,赵宅村“就有数条溪流,从村头流到村尾,一年到头,从不干涸”;而且“江南多雨,乡间多桥,以石板桥最多”,村外由石块垒成的石拱桥,往往“都长满了长青的各种藤蔓,非常美”,是摄影家取景的好地方,也是故乡的诗意所在。因此,作者感激上苍有幸生于雨水丰沛的江南,这是他成年后走进西北的一些地方,“听他们讲如何在二三百米深的地下掘取井水,而且水质不佳时”,自内心生出的感叹。因为在其童年和少年时代,以老家的厨房为中心,“外面有三口井,都不足百米”。而当他前几年因看到石井圈的书,回老家专门查看,发现因早用上自来水,村里当年的三口水井“都已废弃不用”,禁不住感慨,不管是否愿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那个曾经“熟悉的农耕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这些烟雨江南的生活传统和风俗习惯,是作者的乡愁寄托和感怀牵挂,那里乡村的山川、风物、饮食、语调、乡音、虫鸣、炊烟等,随时都会掀起其内心的波澜。
在某种程度上讲,《山河故人》既是回忆录,也是家乡志,更是成长史和自我前传。作者对故乡的回溯,既是一种精神回乡,也是对自我成长与时代变迁的深情凝视,更是一种与自我的灵魂对话,正如作者所讲,“回首故乡,可以安抚自己躁动与喧嚣的灵魂”。但作者对故乡的深情并没有采取直抒胸臆的笔法,而是采用了温和、客观、写意的叙述方式,喜用短文,辅之以简笔线条画和乡村俗语俚语,叙述具有极强的画面感、年代感、仪式感和代入感,又在结尾将对感情和态度的表达戛然而止,形成文短情长、幽默留白、灵动俏皮、充满意趣的格调特色,给我们留下充足的品味和想象空间,回味悠长。如,天台话把妇女生孩子后亲友的送礼称为“望月礼”,把“看电影”说成“望电影”,一个“望”字写出了天台乡村的俗语特色,令人耳目一新,而本村放电影还会请亲戚来观摩,各家为占位置早早将木条凳、竹椅放在晒谷场,十里以内的各村年轻人都会“如赶集般去望”的讲述更是形象逼真,将那个年代的“露天电影”观看场景跃然纸上,以饶有兴致地代入感激发起我们对乡愁的共鸣。
《牛酒》一文里则饶有兴致地讲述了春耕前给牛喝酒的习俗和方法,当读到“酒一喝过,牛便知道一年的劳动要开始了”,是不是感觉很有仪式感和画面感,是不是感受到了作者讲述风格的灵动俏皮。
这就是赵宗彪笔下的烟雨江南,故乡山村的风物风俗风貌,都如故人,乡愁如炊烟,千丝万缕,绵密悠长。浙东山村的变迁,也是作者人生成长的镜像和乡土中国发展前行的时代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