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应峰
读李渔《闲情偶寄》时,窗外天青如靛,秋色正好。我原以为《闲情偶寄》只是“古代生活小百科”,却没想到被他一下子拽进了“快活”漩涡。他写“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写“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写“脍不如肉,肉不如蔬”,字字句句都在教一件事:怎样把沉闷的日子过成戏,把柴米油盐唱成曲,把“生存”活成“生活”。
那样的快活,并非简单的享乐,而是对生命的内在感知,先承认人生本苦,再在缝隙里种花。李渔的“闲情”,是生活密码的用心解读。
《闲情偶寄》乍看是“生活技术手册”;往深里一瞧,却是一套“世间万情的操作系统”。他用剧本替人圆梦,让梦在台上活起来,以衣冠眉目传情,用门窗隔断尘嚣,让器物回握人手,在舌尖点燃烟火,把岁月栽成绿意,让肉身与天地同步,在收笔时一笑退场。
李渔的“闲情”不是空闲之情,而是“让情有闲”:给情感留一条可以自由来去的暗道,使其不被功利轧死。李渔的全部文字,都在偷偷描摹这条暗道的走向。
李渔写剧本,首先算的是“观众泪腺”。他直言:“传奇之设,专为消愁。”意思是说,文人以笔代工,替大众完成情感外包:你不敢哭,我替你哭;你不敢笑,我替你笑;你不敢爱,我替你爱。
我想,当下小视频中短剧、爽文为何火爆?只因现代人与清初观众一样,都需要“情感替身”。
李渔更高明之处在于“反套路”。他让《风筝误》里的韩世勋先因“误会”得福,又让“福”里再生“惧”,观众刚要松一口气,心再被拎起来。悲—喜—惊—疑,四转之后,观众的情感被彻底“漂洗”一遍,出戏时像晒过太阳,轻了三四斤。
“替人圆梦”只是第一层,李渔的终极目标是“教人造梦”——把看戏时那副轻骨头,搬回自己的人生。
李渔论女子装扮,有一句狠话:“美者用之愈美,陋者用之愈陋。”乍听刻薄,细想却是慈悲:装扮不是伪装,而是“帮自己看见自己”。
他教人在额角点“斜红”,在鬓边留“蝉鬓”,无非是把一张脸重新“排版”,让主人与观者同时读到“我”的亮点。
同样思路被搬到居室:小窗可借景,矮墙可藏丑,曲径可延缓脚步。居室与声容,一内一外,共同完成“自我叙事”的展开。
我了悟:情感若只闷在胸腔,会发霉;需要“声容”与“居室”这两层界面,把“我”展开成“我们”——让他人得以看见、得以进入,情感才获得回声。也就是说,给情造一座房子,让它有窗有门,才能被阳光晒到。
李渔写“暖酒杯”,写“四美羹”,写“蒸蟹必用白菊花”,全是“此刻哲学”:人在时间的长河里,唯一能真正占有的,只是“这一口”“这一握”。
他说:“物不求大,足用则佳;味不求多,得趣便好。”这样的“恰好”,谁不愿接纳?因为“恰好”,指尖的触感、舌尖的爆破,都清晰可见。如此,生活不再是“吃饱”与“占有”,而是与物、与味“互道珍重”。
李渔写“蓄鹤”:“鹤之蓄也,非爱其羽,爱其声;非爱其声,爱其与余相忆之声。”一句话,把“养宠物”写成“一起慢慢变老”;写“种蕉”,自承“夜雨孤眠,赖其叶声相伴”;写“艺兰”,说“兰如君子,可共幽忧”。
草木禽鱼,在他笔下都成了“岁月合伙人”:人把生命分出去一点,岁月回赠你绿意、声籁、花香,以及“被惦记”的证据。
都说“时间像贼”,李渔却告诉你:岁月本无情,你若肯把情感“预存”进一株芭蕉、一只鹤,它便肯回赠你“生意”——生之机,活之意。人,一旦把情感种进活物,岁月才能替你浇水、替你开花。
李渔的“闲情”,也有自嘲的成分。他说:“所著诸书,皆足覆瓿。”他认为自己的书只配拿来盖酱缸。还说:“然覆瓿之余,尚有余馨。”他以为,他的书只有盖完酱缸,香味才能飘一阵。
抑扬之间,李渔把人生的“得意”与“失意”揉碎,幸喜“余馨”犹在。
怪不得袁枚写李渔,说:“笠翁,天下之快活人也。”是的,李渔是快活的,他的快活,总是寄寓于“闲情”,先把“苦”咀嚼到位,再吐出“闲”的渣滓;以“情”附加,只解密那一刻,闪现出人性光辉。
李渔的“闲情”,归根结底一句话:“别怕,你可以温柔地活着,也可以温柔地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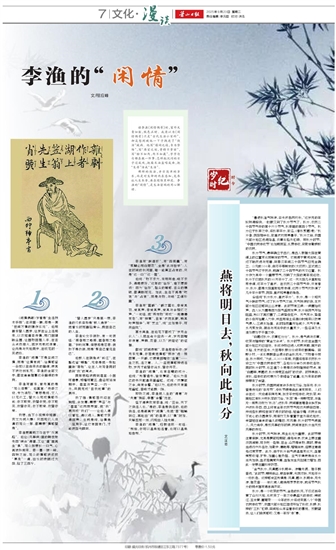
_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