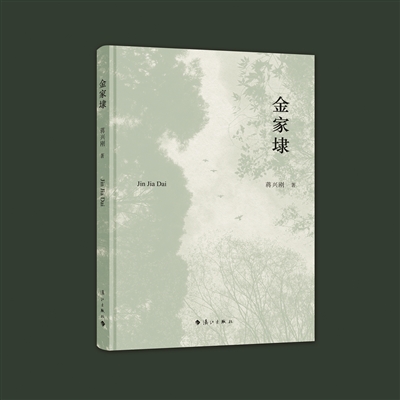■文/ 蒋兴刚
湘湖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萧山的湘湖与杭州的西湖都是由远古时期东海海湾的潟湖衍化而成。北宋时,萧山县令杨时“以山为界,筑土为塘,遂成湖”。明人有记“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境之胜若潇湘然”,遂名湘湖。我出生于湘湖不远一个叫金家埭的自然村落(从空间视角上看,金家埭也属于湘湖的一部分),从小吃着湘湖的茭白、菱角,摸着湘湖鱼虾、螺蛳长大。由于早年围湖造田,湖面大面积萎缩,只剩下零星的水面。在我童年有限的记忆里,湘湖是冷清寂寥、生机肃然的。
湘湖的重生应该和我的写作是同步的。2006年,还湖于民,湘湖完成一期建设,再一次回到共和国版图上。我是有幸的,仿佛是对萧山自身命运的一种反思,回来的湘湖依旧是故乡的、质朴的,“而这种质朴,使湘湖更近乡土、更近自然,更近现代人类越来越认同的人类的终极意义,从而也更近诗性”。
以后的很多年,湘湖的还湖于民一直在推进,我的诗歌写作也一直不曾中断。而这种写作,是一种化解人与自然关系的诗性探索,是对一种新的乡土美学和生存原则的建构。例如诗作《人世间》所写的,“看见几个灰雀的屋顶/雨水欢快俯冲,一切调色板向大地倾斜//发现:雨打、鸟鸣/雨水清洗过的晨光在陡峭的人世/寻觅到了缝隙——//一滴雨落入桃花/一艘船穿过针眼,码头/浮动的沉香/接住了天降的美意”。
出版这部《金家埭》诗集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生活了四十年的村庄被列入了城中村拆迁改造规划。金家埭这个距湘湖几步之遥的村庄,这个我身份证上唯一合法的出生地址,即将被推倒。站到推土机、挖掘机跟前,站在暖洋洋的霞光中,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不是下一个无家可归者?我要把这些年对这片土地的情感用诗的语言梳理出来、记录下来。当然,这种记录是无与伦比的——《金家埭》,“金家河水没有形状/一会儿拿来洗菜,一会儿拿来擦身子/更多的时候/就这样白花花地流淌”。
无可否认,面对环境的急剧变化,焦虑隐藏在自然空间中的每一个具体事物上。而我的诗的文化内涵,尽量把面孔朝向个体的渺小和生命的有限性上。当然,我的主体自我,一定是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涌动着诸多紧张、不安、起伏、隐忍、克制和自我拷问!
这是我个人出版的第四部诗集,离上一部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原本计划全新创作整部诗集,但是在翻阅这几年作品的过程中,一次一次把自己感动,拉回到诗意的桃花源。也罢,就把我这些年行走的诗路都收录在一起。诗集中,既有湘湖、金家河,也有修竹、长空、飞鸟、鱼虫;既有身边的亲情、爱情,也有千里之外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停行走的写作者,但是,我在再远的地方见到的湖,何尝不是湘湖;见到的村庄,何尝不是金家埭;见到的母亲,何尝不是喂给我奶水的母亲……
我以“湘湖之石”为诗集的自序命名,是不是也拔高了自己?我在想,湘湖之石正是因为有湘湖水的孕育,才让它成为一块区别于任何其他石头的石头;才能掂在手中,轻轻一扔,“扑通”一声,余味悠长!
蒋兴刚 男,1976年2月生于杭州市萧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诗刊》等纯文学刊物发表作品一百多组;出版诗集四部。获浙江省作协“新荷十家”作家,杭州市文联青年文艺人才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