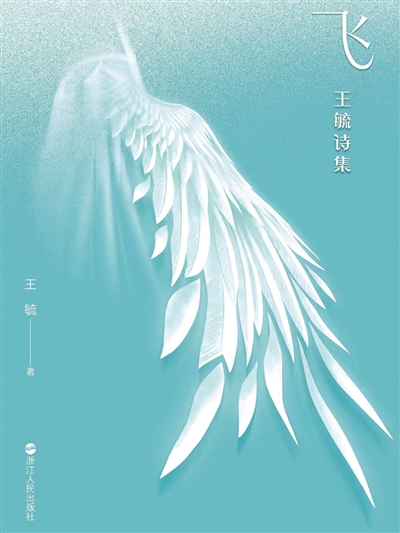■文/ 蒋静米
认识王毓是去年9月的事情,我们聊到各自生活的近况,关于工作,关于婚姻和恋爱,或许由于相似的年纪与境遇,我们都相信我们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彼此没有拘束。离开酒店时,她给我带了一杯奶茶。
根据有限的信息,我猜测王毓是一个热爱生活且饱含能量的人,因为她会在朋友圈分享生活中美好的片段,尽管我们都认为,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沉重和无法预料的变化。她是一个好人缘的人,因为她会分享许多不同人们朗诵她的诗歌的短视频。
机缘巧合,之后她给我打来电话。王毓讲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她会说出许多出其不意的话,给我陈旧的语言习惯带来巨大冲击。比如她会说蒋静米,就算你喜欢天上的太阳、地上的虫,或者动物园里的狮子,我都会祝福你,我会带着贺卡、带着红包来看你。这太诗歌了。她讲述她的家族史,我说你应该写一部白鹿原。是真的,我相信她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不一定要写白鹿原,或许比白鹿原更好,因为我相信为文和为人是一件相等同的事情。
如今有幸受到她的邀请,在此为她的新诗集写一点文字,作为这段友谊的纪念,也作为同为诗歌写作者的一次通信。
《飞》中充满了纯净而忧伤的意象,烂漫的童真在现实的荒原上飞驰,迸发出流光溢彩的思绪,如同用蜡笔在一张透明硫酸纸上描绘出的景象。色彩与画面感是重要的关键词。让我们暂且从两个重要意象中,窥探王毓通过这本诗集构建出的诗歌王国。首先要说到“原野”与“荒原”,荒原是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语,它象征着灰色、衰败、失去信仰和生命的蛮荒之地,正如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一切,不同的时间与纷繁的人物逐一登场,然而我们却无力辨认它们,正如同扭曲的记忆。王毓在《照镜子》一诗中写道:
清醒,抑或沉睡,一起身
我就步入荒原
这宁静高贵的尸身行若沙砾
在心灵的荒原中,一切都失去了完整且值得信赖的参照物。这是一幅自由、宁静而孤悬的图画,一次虚幻的潜泳。王毓的诗歌有一种潜入意识中仰泳的流动之感,既是沉浸于种种自然生命与社会意识的,又是轻盈地越过表象的桎梏,而超然地乘着老庄之道与罗马人的石柱飞翔。王毓为这个空旷的场地布置起了散发出金色光芒的家具,它们是古典式的谷雨、月亮和山花:“四月重复时和月亮一样老/在袅袅的青烟里踉踉跄跄”,是现代都市的情结:“虚弱的魂魄缩进花蕊里/干瘪时就寄居另外一朵”……她调遣着所有充满活力的事物,在笔下形成一场欢乐的聚会,正如《原野》这首诗中所述:
永驻眼前的星彩原来日夜不分
风压过紧贴的火海,低矮的火焰吞没了最后一根青草
水压过干涸的火海,漆黑的灰烬隐没进漆黑的地底
绚烂的爱与自由,正是王毓诗中显目的“星彩”,它是跳跃在青草的火焰、带来光明的消息的精灵,显示出一个诗人独特的心性。在诗歌中,我们总能触摸到诗人本身所带来的人格能量与光彩,而这点,或许比言辞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不想去权力的中心/我喜欢四季如春”,这只精灵带我们远离了权力与历史(这些一成不变的坚固之物,总是令诗歌写作者爱不释手、无法忘怀,然而请别忘了,奥登曾说过“这月色之美,没有历史”……)来到四季如春的没有边际的所在。这是一个由灵性书写的地方,“我的使者是光,眼神是露,足下是河床”,每个受邀之人都将沐浴在露水与河流之中。
这种爱意首先体现在对于人和人性的体认与怜悯当中,对于孩子、老人与女性的温柔。无论是“你守护的孩子们在春天疯长”,或是“她和我就不由得在雪乡遥望远方”,还是“半夜醒来的腹中的饥荒者”,它们所呈现的都是一种先于文明且超越文明的本质的人,这位集诗人、天神与动物的形象贯穿在王毓的书写中,她将自己投射在这种形象的情感称之为“爱情”或是“情欲”。
这种情欲是根植于五感与身体的。“器官是霓虹之城爱的地标”,身体的宝贵等同于灵魂的宝贵,乃是质朴的追寻根源的思想。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来自名为母体的幽谷。在王毓的诗中,身体与自然是互相映照、互相生成的关系,“海的漩涡”与“耳蜗”、“跑马场”与“你的额头”、“山脉”与“鼻梁”,人的形体被舒展于大地之上,如同夸父逐日倒下后化为了群山与流水的古老神话。因此,这种爱与宇宙的潮汐拥有共同的呼吸和命运,显示出极其沉浸体验式的生命观念与文学观念。
有些眼泪是为了乞求被施予珠宝
一些眼泪本身就是珠宝
流露我们共同的命运
流露世上爱人的慈悲
流露无光处不明了的所在
人与自然的联结,自然带来人与人的联结。世界上的每位爱者都身处于同一种命运当中,这是一种光明的命运、珍贵的命运、鲜花与光环的命运。“树木和他结合在一起/就是我在人世居留的所有生命”。当人类那些短暂的情绪融入源源不断的循环当中,更为恒久的生命就诞生了,从“易朽的爱情”变成了不间断的美与善。
这种提纯度极高的情感,已经漫溢出了爱情的范畴,演化为一种围绕着自然万物的怜爱:
如果非得烧成灰
就把我埋在那棵柏树下
柏叶香、猫头鹰绕圈圈
要是满天飞着雪
就把我撒在操场上
年年有数不清的孩子
在我头顶跑过
所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亡是一扇通向新生的门扉,而孩子的脚步声会年年踏过不同的雪和草地。“请不要与名利为伍”,这已然道出强烈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落点又是非道德化的,“追随名叫虚空的访客献出可爱的花朵”,这是如此纯粹、活泼的追求,如同花朵一样,装饰荣华,并不由于什么,也不为了什么。
这位爱者的形象有时以男性的面貌出现,有时则以母亲的形式出现。或者说,母亲更具有象征式的意味,她“有永不干涸的爱意/允许这个卑微的孩子/和她卑微的爱情慢慢死去”,并且许诺“睡在我广博的怀中/永远地活在未来幻想的建筑里”。母亲同时掌管着生与死,出于对孩子的爱情,她可以放任孩子追随危险和欢乐的爱情而死,同样的,她也应允她的孩子在爱与美的幻想建筑中永生。对于她来说,“云儿是故乡,我才是远方”,母亲原本是自然的化身,为了她所诞下的生命而奔赴陌生的远方,在这条尘世的道路上辗转。而在将来的一天,她会乘坐着虚幻的飞机回到天空中的故土。王毓将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性编织为动人的寓言,一个事关活着与死去的寓言,一个从子宫到天堂的寓言。它说的正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如果说我对于这本诗集有什么可以辩驳之处,或许在于一个疑惑,现实并非一种童话式的真空环境,美、善与爱如何在晦暗难明、错综复杂的情境中生存?这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人本身的纯真是否能作为一种回答?对此我感到没有把握。“我的眼,要不要朝向远方的花园”,朝向未来的诗歌,永远在诉说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何处。而那目光所向的地方,即是我们最终将抵达的地方。希望时间将告诉我们答案。
(蒋静米 90后,浙江嵊州人,写诗,兼事小说创作,辑有诗集《互文之雪》《苦海游泳馆》,曾获第六届复旦“光华诗歌奖”、第五届“徐志摩诗歌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