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跳
“只剩下最后一碗饭了,我一定让给李光头吃;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了,我一定让给李光头穿。”
这是宋钢在李光头的亲生母亲李兰即将去世前做出的承诺。但我没想到的是,一句承诺,一生兄弟,这不只是让即将逝去的人感到安心的宽慰,宋钢确实用他的一生切切实实地践行了这个承诺。无论身处什么境地,他都在挂念着李光头,都会时时为李光头着想。
《兄弟》是一部体现人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余华老师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最打动我的莫过于它的真实感,但这不仅仅是全然的真实,真实中似乎又交错着合理的荒谬,让人不禁莞尔,抑或皱起眉头。同时,我也被余华老师细腻的文笔和情感流露深深地感染,都说人只有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但余华老师的文字却有不一样的魔力,这些文字能够触动人心底柔软的部分,将我带入书中的环境里,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李光头和宋钢,没有血缘关系,两兄弟的性格被刻画得截然不同,李光头精明、粗鲁、自负,但他重情义、有头脑和胆识;宋钢善良、腼腆、为人老实,但他懦弱、内向、缺乏自信。他们的性格就像镜子的两面,他们的人生轨迹也是相反方向的箭头,各有各的落魄,各有各的精彩。这对异父异母的难兄难弟,一个从穷光蛋到千万富翁,另一个却从爱好读书到卧轨自杀。
余华就像是一名冷静犀利的外科医生,他以笔作为手术刀,将人性中好的坏的、发光的腐烂的部分全部用刀划开,让其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兄弟》带来的真实感主要是时代的真实、人性的真实。余华老师总是能用最朴实的文字写出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其中也蕴含着他作为作家独有的悲悯情怀。这本书中主要囊括了两个时代。特殊时期人人自危,李光头和宋钢便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担任“父亲”这一角色的宋凡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都是一个完美的、绝对理想的正面形象。这样一个待人厚道、温暖的人,却落得个在车站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下场,让人不由得握紧拳头,为之叹惋。像宋凡平一样,那个时代的一些人是竭尽全力地生存,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把自己的尊严放低到尘埃里,顽强地挣扎。后半部分,笔锋一转,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李光头和宋钢开始走上社会,寻找不同的职业,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李光头是个商人,他的油嘴滑舌和聪明精干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助力,让他在经历几次风波后成为不愁钱花的大富豪。而宋钢由于过于忠厚老实,脸皮又薄,尝试了很多份工作都没有办法长久地做下去,还不幸染上了病症,途中甚至为了卖药去隆胸,拿身体和生命去赚钱,想要让家中的日子好过一些。当他终于赚到一些钱后回到镇子,得知妻子出轨了李光头的消息,至亲至爱的背叛犹如晴天霹雳。宋钢变得心灰意冷,但没有过多地责怪他们,而是一个人在痛苦中卧轨自杀,安静地死去。
书中强烈的对比感也是我较为欣赏的部分。在阅读的过程中,多处强烈的对比让我想起了雨果所说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余华笔下的李光头和宋钢既有美又有丑,既有恶又有善,他们的形象也因此更加丰满立体,像是真切地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活生生的人。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之一是李光头在广场上静坐示威,变成一个蓬头垢面风餐露宿的流浪汉。宋钢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都会路过,与李光头相遇。李光头见到宋钢总是会一番诉苦,宋钢就算多次答应林红不会再给李光头任何帮助,但当他遇到李光头的时候,都以心软贡献出自己的饭票为结局。宋钢对李光头的深厚情感是刻在骨子里的,甚至不惜与林红发生争执。在兄弟与爱人之间,宋钢就像钟摆一样不断地摇晃,一会儿摆到李光头这一端,一会儿摆到林红这一端,但哪一方都无法全然地割舍。
有人说李光头对不起宋钢的这份情义,也有人说李光头从始至终只在乎他自己。没错,李光头是个实打实的“狠角色”:他千方百计阻止宋钢和林红在一起,又在宋钢离开镇子去赚钱后私通林红……种种事迹,固然可恶。但他的心里从来不是只有自己,他会在当上厂长后第一时间想到和兄弟分享,会在办垃圾场赚钱后打算和宋钢分享财富,会在知道宋钢得病后基于对他的了解,通过委婉的方式帮助宋钢治病疗伤,这些也是事实。由此,我又不得不佩服余华老师刻画人物的能力,引导读者跟随人物的情感。或许在上一章,我还因为李光头的死皮赖脸感到恼火,但在下一章,就有可能因某个小小的举动而感到暖心,想着这个人似乎也不是这么坏。我对人物的情感和看法也随着情节的波折而不断起伏,最终在脑海里雕刻出真实的、立体的人物形象。
文章的最后是三个人走向各自的悲剧。在宋钢卧轨自杀后,两人瞬间都醒悟过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的林红觉得自己是个浪荡的“婊子”,于是破罐子破摔,美其名曰开了一家理发店,实际上却是妓院,她每日以笑容示人,担当着妓院的打理者。她下半辈子都在借此寻求自我安慰,心理的救赎。李光头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不同于往常,这一次宋钢的死让他彻底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真正的孤儿,世上和他最亲密的兄弟已经不在了,即使有万贯家产,无数美女也无法填补他内心的孤独,所以他提出要带着宋钢的骨灰去太空,让宋钢的骨灰停留在太空。文章是这样写的:“李光头的眼睛穿过落地窗玻璃,看着亮晶晶深远的夜空,满脸浪漫的情怀,他说要把宋钢的骨灰盒放在太空的轨道上,放在每天可以看见十六次日出和十六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上,宋钢就会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了。”读到这里,我不免再次感到些许动容。这是如此动人的文字,炽烈的情感。李光头依然渴望兄弟的陪伴,希望兄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不被打扰地安息。被隐藏了许久的兄弟情再一次得到显现。
余华老师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的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或许命运正是真实与荒谬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吧,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反抗,无法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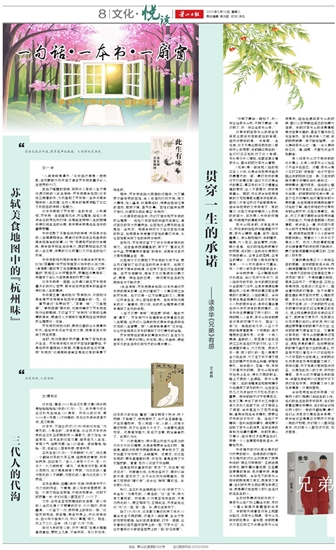
_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