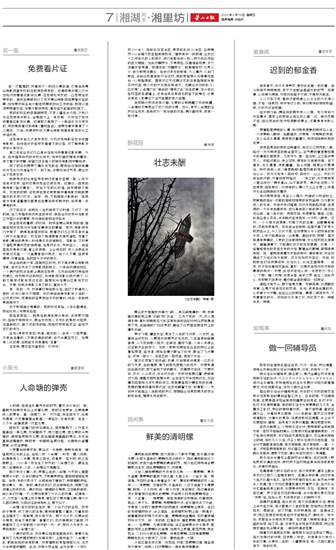■祝美芬
在一次整理时,我看到了一封已泛黄的信,它是当年萧山电影院宣传科的汪越涛老师写的。记得那是我第二次参加杭州市青春奖影评比赛,汪老师托学校的一位老师给我带来的。信中主要跟我谈了关于萧山电影院免费看片证的事,说如果我毕业后分配在城厢或附近工作的话,就可以继续使用看片证,如果分配到别地,看片证只能暂时收回了。
那时的我正就读湘湖师范,不怎么懂社会交际,之所以与汪老师有点联系,全是因为上一年我第一次参加了杭州市青春奖影评比赛。记得那次是用了一个晚自修匆匆写好的,写的是刚看过的电影《屠城血证》,结果无意中竟得了个二等奖。之后,我便被吸收为萧山电影院首批影视评论工作组成员。
汪老师先后几次徒步来校,为我送来电影杂志与中国电影报。他说估计我在学校里看不到这些,对了解电影与写评论有好处。
第二年他让我们几位再参加杭州市青春奖影评赛。为此,他专程来到我的学校找到我,说学校里环境有点嘈杂,写文章不够安静,希望双休日择个时间去电影院安静地写。
到了时日我便带了稿纸与笔前往,哪知他仔细到连稿纸与笔也为我准备好了。到了后,没等我缓过气来,便让我坐下来赶紧写。
就像考试时会有监考老师过来看你答题一样,心中不免有点紧张,但我还是安抚自己赶紧写。记得这一回写的是电影《摇滚青年》。开始下笔时比较难,后来便顺了起来。我写的时候,汪老师在旁边默默制作着电影放映前要播放的手写幻灯片。后来一问,才知道每次影前的一些预告与观影温馨提示都是他在幕后亲手制作的,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字。
过了些日子,他就托人给我捎来了这封信,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专程来到我所在的学校,亲自给我送来参加影评工作座谈会的请柬,并仔细地告知活动地点。
毕业那年的暑假,我收到一封来自萧山电影院的信,信里告知我去杭州参加影评赛领奖的事宜。那天,电影院专门安排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载着我们几位获奖者去省人民大会堂领奖。我见到了导演谢晋与演员潘虹,观看了电影《最后的贵族》,听说是该片的首映礼。观影后,又欣赏了潘虹声情并茂的诗朗诵,她身材修长,气质出众,一袭宝蓝色紧身连衣裙,看上去很美。上台领奖时,我从冯根生手中接过奖品——六盒青春宝口服液。他个儿不高,但很有精神,笑意盈盈,当时四十多岁的样子。
毕业后的前六年,因离城区较远,我不再去萧山电影院观影,自然也失去了与电影院的联系。六年后我调到城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遇到汪老师。几天后他就打电话到我单位,说我既然已到城区,去电影院观影也就方便了,以前又是写过影评获过奖的,推荐我参加萧山区影视家协会。于是,我就与电影又有了联系,直到今天。
有一年的一天,我有事打电话联系他,但打了数遍无人接听,这与以前大不相同。我打电话向原来影评小组的一位成员打听,可得到的答复却出乎我的意料,说他一年前就患病离开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时我还年轻,父母也都健在,而他比我父母更年轻些。
那些年那些人,就像汪越涛老师这样的,本来素不相识,但由于种种缘分,便给予我那么多无私的帮助与培养,如温暖的灯,暖了我的来时路;那些叮咛那些笑容,留驻于记忆的深处……
正如《寻梦环游记》所言,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只有当活着的人不再记得的时候,他才会真正死亡。如果有人还记得,他就能永远幸福地“活着”……
汪老师,愿您在天堂那边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