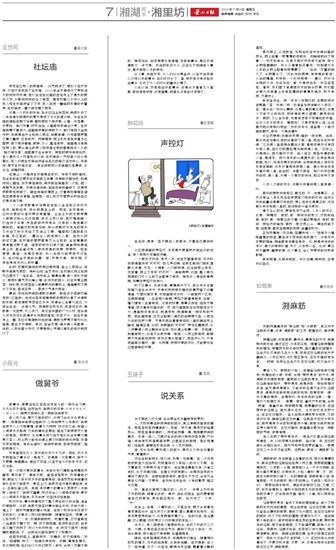■蒋兴刚
写完答应别人的朗诵诗,一口气就泻了,想找个地方走走,不知不觉来到了社坛庙。2019年金家埭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城中村改造,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走上了漫长的搬迁之旅,分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唯有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社坛庙被留了下来,老人住进一幢临时改建的安置房,社坛庙被一圈大铁皮围了起来。
这是一个初秋的午后,拆迁已经尘埃落定,就像扒去了一件在漫长而溽热的夏天浸透了汗水的湿衣服。去往社坛庙的道路在脚下延伸,睹物思故勾起伤感,心里一片落寞一片素白。庙门开着,叮叮当当,从里面传来诵经之声。社坛庙规模不算很大,但里面供奉的神明不少,前门有四大金刚守护,中间是当方土地陈二明王,后殿新建,为观音菩萨塑了高大雕像,慈目威严。两侧厢房,楼上形形色色供着多位菩萨,楼下用作管理,厨房、办公,整洁有序。庙里是没有常驻师父的,带头诵经的师父和穿居士服的都是四邻八乡的“超级爱好者”,但都属于业余爱好。早些时候母亲告诉我,自从周边几个村堂拆迁以后,社坛庙的人气和香火已今非昔比,老人们把社坛庙当作留给自己的超级活动中心;母亲说,幸亏社坛庙还在,一有空闲就可以去庙里找些事做,念念经,消磨时间。
记得上一次踏进社坛庙是在年初。母亲不知听谁说,本命年的自己要去社坛庙做三件事:去佛前讨碗饭吃;和佛说说心里话,祈求佛祖保佑;离开前在庙里洗一次脸,把一身晦气洗洗掉。我虽将信将疑,但在母亲的催促下,还是恭恭敬敬地照做了。跪在寺庙的蒲团上,对着佛陀喃喃自语现在想想有点滑稽,但是那一刻心底对于菩萨会护佑自己还是深信不疑。
一个人的宗教意识如果自觉地从生活现实中成长出来、超越出来,快乐就是至上的。现在,社坛庙由一位叫木根的长者负责日常管理。土生土长的木根师傅从前跑过码头见过世面,年纪上来以后,把打理庙里一切当作了日常,并且做到井井有条,这样的人是有高级趣味的。庙里风物别有况味,枝头被剪成光秃秃的茄子又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结上了果。墙面和门窗刚做过粉刷,朱红色的,一靠近让人就有种代入感。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社坛庙的菩萨都是灰头土脸的,坐在高高的佛龛里沉默不语。但那时的我们很大胆,偷偷爬到佛祖身上去,甚至偷过别人虔诚供佛的甘蔗、苹果吃。现在想想,佛祖一定是慈悲的,我从未因为越界而疼过肚子,他们和金家埭的长辈一样,严肃只是一种法相,不存在身体与内心的较量。
此时,挖掘机推倒的民房已是废墟,登上二楼阳台,视野开阔再无遮拦。柴岭山远,金家河近,社坛庙这块土地陡然凸显成了一座孤岛。缓步岛上,触景生情:前人写秋天回乡,常用秋高气爽比喻心境,此刻我的回乡,似空中莫名飘落一阵秋雨,秋雨落在从前最熟悉的事物上,偏偏事物又夷为了平地,香消玉殒……悲凉之气油然而生。
最后,来说说民间的道教与佛教。前些日子读胡竹峰写的《三祖寺》,他说近些年接触佛教的同时也看了点道教的东西,感觉道教考虑自己多点,可谓全心全意为自己、为世俗生活,一派烟火气。而佛教主张无我,或者说忘我,佛教是一元世界,不二法门。其实在中国的广大乡村,世俗烟火与无我无私的清寂永远同时呈现、紧密不分。在社坛庙走上一圈,本应该是道教场地的庙,佛教元素毫不排斥比比皆是,甚至多于道教。或许,在金家埭,道与佛从来都是一体的,从来未曾分开过,只要是块心灵得以寄托的地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