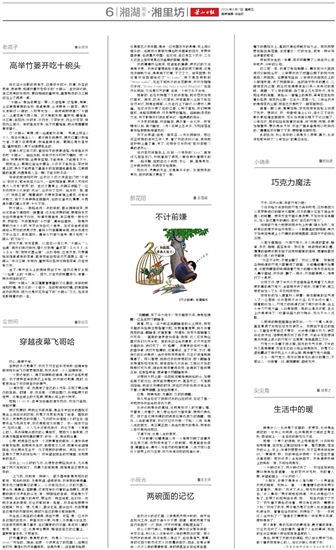■余观祥
到达绍兴马鞍的表弟家,已是中午时分,热情、好客的表弟、表弟媳,知道我喜欢老底子的“十碗头”,在我到达前,油红透亮的东坡肉、黄白相间的鲞拼鸡、晶莹剔透的汤三鲜已经上了满满一桌。
“十碗头”是当年萧绍一带人办结婚宴、订婚宴、寿宴、上梁宴等宴席的俗称,每桌宴席,必须要有10碗菜。偶尔也有超过10碗的,人称考究加一。由民间厨师掌勺“十碗头”,上桌菜肴大同小异。依次是前东坡、鲞拼鸡、醋熘鱼、汤三鲜、后扣肉、炒时件、炒肉皮、冬菜粉皮、肉丝炒芹菜、榨菜肉丝蛋汤。有时鱼类紧张,烧不成醋熘鱼,就会用糖醋排骨来替代。
办“十碗头”宴席,用八仙桌配长条凳,一张桌上可坐8个人,每条长凳坐2人。桌子南北向摆放,摆放位置以板缝为准,办酒及日常用餐,板缝呈南北向。朝南位是长者专座,懂规矩的人是不会随便乱坐的。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堂姑妈家的表哥结婚,母亲指派我去吃“十碗头”。临出发前,母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吃‘十碗头’吃要有吃相,坐要有座相,不能猴急;不能南北不分,一屁股坐上,朝南位留给长辈坐,小孩子不能抢坐;菜送到桌上时,筷子不能像鱼叉戳鱼似的在碗里乱戳乱捣;三鲜碗里的鱼圆、肉圆是每人各一颗,不能多吃多占……”
母亲的教诲和叮咛,让我这个初次独自出门吃“十碗头”的孩子,感受到压力山大,一旦吃相难看,要被人家说成是大人没有“教养”的。在这次喜宴上,我确实领略了一位长我两岁小伙伴的“风采”,让我长了见识。他与我一样,第一次“独闯江湖”,喝喜酒时,只要有菜肴端上桌来,没有半点斯文,迫不及待伸筷往碗里夹,他的这番失礼情景,令同桌长辈们眉头紧皱,十分不悦。
吃十碗头,一般路途远一点的亲戚,都会提早到来,而近邻却舍不得因吃一顿喜酒,过多地浪费时间,要等到东家发出开席信号才行动。所谓开席信号,其实是用一根长竹竿,顶部扣一只拔草用的“小竹篓”,高举出屋栋。一般是开席前约半个小时,东家会发出这个信号。左邻右舍或在田间地头劳动的被邀对象,看到小竹篓高高举起,就会迅速放下手头活儿,赶赴酒场。高举小竹篓为信号,是沙地吃“十碗头”的习俗之一。
时光不再,岁月荏苒。20世纪80年代末,“十碗头”“八仙桌” 离我们渐行渐远,替代它的是“叠式菜”(菜配得多,盘上叠盘) 和“旋转式圆台面” ,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只要高档宾馆餐桌有的菜肴,都有可能出现在农家酒席上,但“十碗头” 中汤三鲜、东坡肉、鲞拼鸡这些传统特色菜肴,仍在传承之中。
当下,虽然舌尖上的美味层出不穷,但我还是怀念那“八仙桌”上的“十碗头”。因为,它在我的味蕾深处,有着一种渗透性的记忆。
而吃“十碗头”,其实蕴藏着厚重的文化基因,母亲的教诲和叮嘱,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她的教诲和叮嘱,时常回响在我的耳际,因为这是我慈母留下的“十碗头”文化,她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