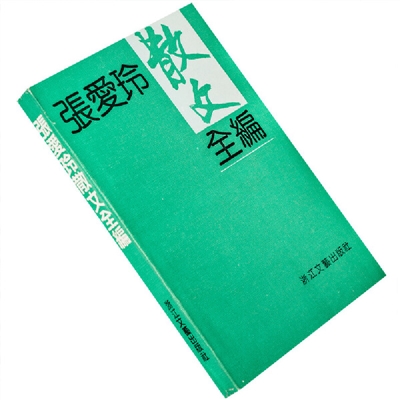文/ 王旭东
“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读《张爱玲散文全编》,当张爱玲的“谈话风”徐徐向我们吹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平和冲淡的凉爽。
这种清凉使我们暂时抛开尘世的烦嚣,诗意地欣赏着如水般漂走的世俗生活,让我们对那种本应细琐无趣的生活保持一份悦纳的心境。你看,张爱玲在淘米时会对发现一条胖虫而引发阵阵惊喜;在买菜时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欣赏油润的茄子;她更会在服饰的变迁中解读人性与民意。张爱玲就是怀着那份深切的恋俗情结,在庸常的物质中,在柴米油盐的怀想中,在水与太阳的润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是一个能充分体味人生,享受世俗意趣的人。
然而,如果张爱玲是真正地沉迷在世俗深处而没有审美距离的话,她是写不出这种平和隽永的文字,也不可能产生对人生的种种看法。她其实是站在世俗的高处,用审美的眼光在打量世俗,对世俗生活有着一种热爱,沉入世俗又有独特审美,她需要用世俗的欢愉,冲淡郁闷的情思,使世俗成为她心中无数块垒的泄洪道。就这样她一头扎进了世俗,在世俗的世界中乐此不疲。
艺术,是她心灵的栖居地。服饰、电影、舞、公寓、路景这些世俗物质,仅仅是她精神栖居世界里“有意味的形式”罢了。“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地威胁”,在她眼里,“生命只是一袭华丽的、爬满了蚤子的袍”而已,这种生命的残酷感时时冲溢在胸,撞击着她柔弱的身躯,对人生小趣表现出感官上的需求和喜爱,以此寻求存在的意义。正如她自己所说,听见电车响才能入眠,因为电车回厂给她一种“回家”的幻觉,使她那空落的心有一种精神上的归依感。这就是她不厌其详地描写“克林、克赖、克赖、克赖”电车铃响的原因。这也是她沉迷世俗以求救赎的内心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