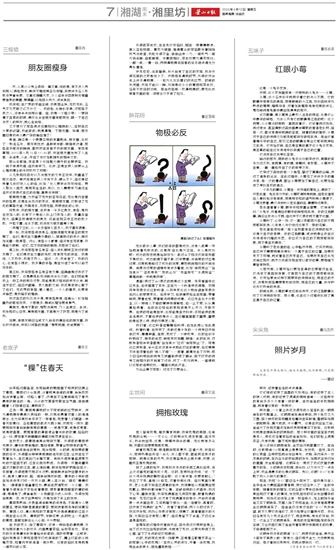■陈女
近来路过甜品店,发现临街的橱窗里不知何时已摆上了青团。青团们个头饱满,泛着明亮油润的深青,挨挨挤挤地占领着台面。过路人看了,仿佛在不经意间窥见了春天最柔软鲜活的一角。淡淡的艾草香弥散在空气里,悄悄提醒着人们阳春已至,清明到了。
江浙一带,青团是清明时分不可或缺的应节糕点。作为清明粿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它既包裹着对昔人的绵绵思念,也为日常饮食平添了一抹春色,抚慰着人们渴望一尝春天的胃口。各地青团的做法大同小异,然而无一例外,都要用到开春后新鲜柔嫩的青草——或是艾草,或是浆麦草,或是鼠曲草。葳蕤春草的清香混合着米粉的软糯,轻轻咬上一口,便觉春天暖融融的清甜滋味荡漾在舌尖。
在我家乡,做青团通常会用到艾草。外婆做的青团讲究颇多,糯米粉要新磨的,雪白细腻,带着谷物特有的香气;艾草只挑当年新生的嫩叶,现采现用。小时候,每到要做青团的日子,外婆都会早早煮起提前泡好的红豆,让我在灶下帮着烧火,自己再出门采摘艾草。待到外婆挎着盛满嫩艾叶的竹篮回家时,红豆也刚好熟透。外婆用一只搪瓷罐来盛滚烫酥软的红豆,撒上绵白糖,麻利地用铲柄捣出豆沙。紧接着,外婆把嫩艾用滚水烫熟,稍稍晾凉后拧出碧绿的汁子,再混入糯米粉,略一搅拌后揉成粉团。青绿的小块粉团在她手中变幻成一只只小碗,裹入豆沙后,“碗边”慢慢收拢,一道道褶子堆叠着拉长,最后在顶端聚成一个小圈。我看着外婆有条不紊地包着青团,想象着青团甜香软糯的味道,等得急了,便偷偷挖一小块甜豆沙送入口中。外婆发现后微微一笑,并不出声呵斥,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青团蒸熟后,外表呈润泽鲜亮的深绿色,不由得令人想到碧玉,想到河畔湿漉漉的青苔,想到被春雨洗净的旧青石板。青团入口,清淡柔和的艾草香气与绵润清甜的红豆沙一同在舌尖化开。清明时节,乍暖还寒,此时吃上一只温热的青团,香甜如暖流沁入心田,十分熨帖。
在 我的家乡,除了青团外,还有一种白色的清明粿,外形如同手掌大小的饺子,内里裹着菜馅,俗称菜包饺。菜包饺的外皮是糯米粉掺着籼米粉做的,绵软中带着一丝韧劲;馅料则是将冬笋和豆腐干切成细细的丁,羼上切碎的小段腌芥菜,和着肉末或油渣一起炒熟。这样的馅料本身就是一道爽口的小菜。
外婆做菜包饺,往往先炒好馅料,搁在一旁慢慢晾凉,再从容地和面。青花大碗里,堆得冒尖的菜馅散发着阵阵热气与咸香,我趁外婆不备,悄悄舀走一勺,一面吹气一面大快朵颐,倍感鲜美。与青团相比,菜包饺更为清爽可口。一甜一咸,一青一白,两种清明粿将阳春的日子装点得尤为隽永缱绻。
岁月悠悠,流年暗换,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与外婆见面的次数愈发少了。然而每年清明时节,外婆依然会包上许多清明粿,一一地为儿女孙辈们送去应节。时间的长河里,天地不能以一瞬,反倒是这小小的青团和菜包饺,经年不改旧时滋味。每当我拈起一枚清明粿时,便无比庆幸春天里的每一缕思念终于有了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