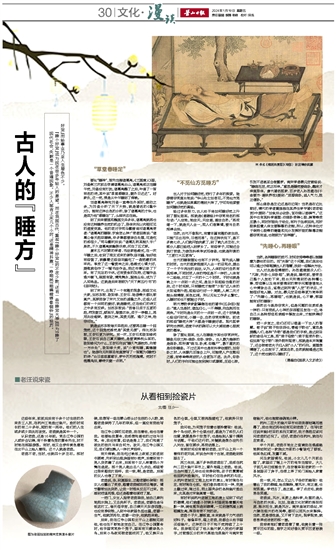文/图 汪少一
这些年来,前前后后有千余个讨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杭州工地捡过瓷片。捡的时间长的有二十多年,短的有一两年。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因此而改变。老苗就是其中一个。
认识老苗,还是16年前。常去江寺公园的人或许会记得,有个拎着鸟笼的算命先生,时不时地在那里游荡。有时,他又会穿件黄色僧袍在北干山上给人看相。这个人就是老苗。
老苗不老,当时,也就四十岁左右。那时候,我想写一组在萧山街头讨生活的小人物,就跟老苗保持了几年的联系,但一直没有把他写出来。
在江寺公园初见老苗,我在看他,他也在看我。他要给我算命,我却想知道他的过往与日常。命,我没有算,但话是搭上了,我们知道了彼此的姓氏与来自何方。改天,在江寺公园又见,我们便如熟人一样打声招呼。
有天傍晚,我在吃过晚饭上夜班之前逛到牛脚湾,先听到出租房里有吵闹声,后看到有个男人突然蹿了出来,后面有个女人举着把小方凳在追赶。那个男人跑出去八九步远,却猛转过身来跟我打招呼。我一惊,啊,是老苗。后面的女人也停了下来。
老苗说,走,到屋里坐,正跟老婆吵架呢!那女人也露出了笑容,跟着老苗喊我进去喝茶。情节翻转如此突然,让我一时根本反应不过来。我感到进退两难,但还是跟着他俩进了屋。
一进门,女主人指使老苗陪我,她自己麻利地把水烧上,又去洗杯子。老苗说,老婆在金马饭店打工,每天很辛苦,自己嘛天天东游西荡,也没有挣到钱,人到中年家里负担也重,老婆一生气,他就顶两句,老婆一动手,他就起来跑。
后来,我在江寺公园和北干山上都能见到他,他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在江寺公园算命时,他手里常常拎个笼子,里面有只嫩绿色小鸟,后来小鸟夜间被老鼠咬死了,他又换只白色的仓鼠,仓鼠又被流浪猫吃了,他就拎只空笼子。
我问他,为何笼子空着也要拎着呢?他说,拎个鸟也好,拎个仓鼠也好,都是为了吸引人们注意,就算是拎个空笼子,也是给别人留个猜测与话题。干他们这行的,关键就是想办法先引人关注,留住脚步,再把话搭上。
有段时间没有看到老苗,北干山上另一个看相的老刘说,听说台州有个古城,老苗跑到那里去了。
两三年后,差不多快把老苗忘了,我却在杭州二百大瓷片早市上,意外地碰上老苗。他说,在台州混了几年也没有挣到钱,孩子的舅舅喊他回杭州捡瓷片。平时他们住在余杭的勾庄,从杭州老城区工地上拉来的废土,有时倒在勾庄,有时倒在仓前。他们像找落花生一样,把废土翻过来,倒过去,把土里夹杂的各种瓷片捡出来,尤其是对宋瓷高看一眼。
有时听说杭州老城工地的废土运到了邻近的德清,他们就像小时候乡村里赶场看露天电影一样,骑电瓶车追到德清,一见到建筑渣土就眼睛发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老苗个子大,腰板直,本来就是干力气活的好料子。每逢早市,碰上老苗,我都会从他手里买些瓷片。这样的日子不知不觉持续了上十年。我亲眼见证了他从瓷片新人变成行家里手,对较难区分的宋代黑胎龙泉瓷片与南宋官窑瓷片,他也能较准确地分辨。
杭州二百大的瓷片早市终因资源枯竭而落幕了,我也有近两年没有见到老苗了。在写《老汪说宋瓷》栏目的系列文章时,我才想起应该问问老苗的近况了。还好,老苗仍在杭州,就在勾庄卖菜。
半个月前,老苗尽地主之谊请我在逸盛路地铁站附近一家烧北方菜的小餐馆吃了顿饭。他面色红润,发量不减。
问及家里情况,他说,小女儿几个月前出嫁了,家里买了辆上十万的电车当嫁妆。大儿子前几年已结婚生子,在安徽阜阳老家的一个县城里买了房子,在街上弄了间门面给人家看风水。
我一惊,问,怎么又让儿子走你的路呢?他看出了我的疑惑,给我解释,看风水,有正道,也有邪道。学进去了,是正道。学了点皮毛,就容易走邪道。
老苗说,风水,本质上是科学,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良渚文化时期的择阳而居、择水而生,就是风水。南宋皇城的选址,宋六陵在绍兴的布局等,都可以用风水来解释。当然,若是悟性差,又不肯下功夫,现学现卖,就容易弄成迷信的那一套。
我惊奇地盯着老苗看了看,他竟长着一张贾平凹似的脸,眉宇之间好像比贾平凹更舒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