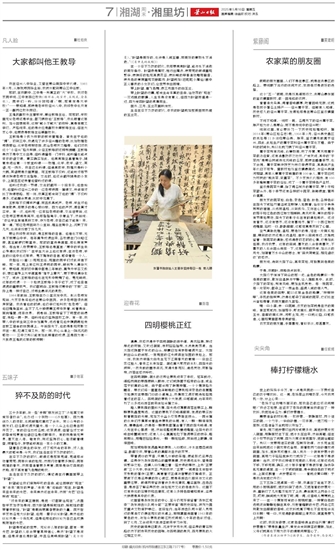■杜柏良
我在绍兴八中毕业,又曾在萧山南阳中学代课。1981年8月,从原杭师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萧山三中任教。
那时,在我眼中,三中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校。我对老家同学说,三中有四位校长(楼祥永、赵宝升、王绳武、俞泉钦)。同学们一听,纷纷附和道:“啊,那肯定是大学校!”——要知道,即使是老学校绍兴八中,我印象中也只有一正一副两位校长而已。
王绳武副校长主管教学,兼任教导主任。可那时,学校里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习惯称他“王教导”,我也跟着这样叫。如今回想起来,这种“喊小不喊大”的称呼,真是有趣又亲切。严格说来,他的身份应是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但在大家心中,他更像是教导主任兼副校长。
王教导是个极为称职的教学管理者。首先在于他的“博”。初到三中,我遇见了许多绍兴籍的老师,比如物理老师蒋菊仙、化学老师柳志刚、政治老师方之耀等。他们对我这个“小绍兴”格外照顾,介绍王教导时还特别提醒:王教导虽然不是中文系出身,但听得懂每一门学科,能听懂也能点评你的语文课。事实确实如此。他常常抽空拿着凳子,随意走进任意一个教室听课——物理、化学、数学、语文、英语,无一例外。我自己也听课,但通常数学、物理只是听个大概,英语更是云里雾里。可王教导不仅听,还能针对每节课与授课老师交流指导。交流时,他还会翻开随身的小本子,上面密密记录着他曾听过的课。
他听过我的一节课,交流时翻开一个旧本子,他告诉我,他曾听过绍兴二中的一位老师讲同一篇课文,并详细对比了授课思路。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他的“博”:不仅听得多,还能融会贯通,比较中见高下。
王教导不仅博学严谨,而且极具威严。老师、学生对他虽有敬畏,却更多的是心服口服。因为他的严厉,源自真才实学。有一次,他听完一位年轻老师的课,交流结束后,这位老师正要起身离开,他却指指凳子,示意坐下,然后说:“你让学生背诵某段文字,作为老师,你自己能不能背?来,背一遍。”那位老师回到办公室后,瘫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几天,也深深反思了好几天。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王教导的自信。他谁也不服,尤其不服萧山中学。每年高考成绩出来,各校便在门口贴红榜,甚至敲锣打鼓宣传。那时的宣传虽简陋,却也颇有声势。每当有人称赞萧中,王教导总是直言:“萧中的学生未必考得比我们好!” 在学生大会上他这样讲,在与老师、学生的谈话中也这样讲。毫不掩饰的自信,感染着每一个人。
我担任83届(2)班班主任,班里的同学们对此深信不疑。那一年,班上有位叫王伟明的同学,顺利考入清华大学。要知道,那时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的,高考升学率又极低,想应届考上大学简直是“难于上青天”,更不要说清华北大了。或许,王教导的话也在无形中鼓舞了他。毫无疑问,这样的成绩一个一个地被王教导小本子记下,成了他自信满满的重要底气。我们都明白,王教导对萧中的“不服”,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对师生最深沉的激励。
1984年前后,王教导在办公室突发中风。赵淡老师发现后,大家紧急将他送往萧山中医院。许多老师陆续去病房探望。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仍亲切地叫我“杜老师”。但他已嘴角歪斜,坐不了几分钟便需王师母扶着,斜着身体,面向墙壁,闭目休息。 病愈后,王教导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走路一瘸一拐。但听说他仍坚持回校工作。有一年,我带八中的学生到三中参加高考,远远看见他步履蹒跚地走在教工宿舍的林荫道上。午后阳光下,他的身影和树影交织在一起,拉得又细又长。那一刻,我心头涌上一阵沉沉的感动—— 三中之所以能有如此辉煌的成绩,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像王绳武这样的教师啊!